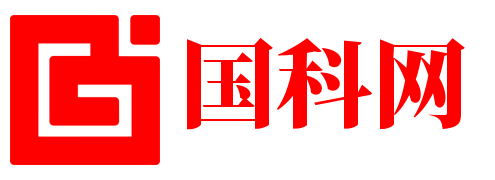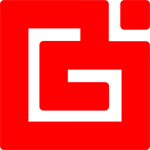近日,我参加航空工业电测营销党支部组织的红色学习教育,踏入四川两弹城,时间仿佛在这里凝固。
斑驳的红砖墙,简陋的平房、办公楼,蜿蜒的防空洞,无一不在诉说三线建设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
三线建设承载着国家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这段从国家前途命运考量的建设历史,改变了若干人的命运轨迹,亦深刻改变了中国的工业格局和工业化进程。因为三线企业的特殊性和保密需要,崇山阻隔着企业与外界的沟通和交流,也阻隔着三线人与外界的关联。在三线,厂矿、医院、公安、学校一应俱全,俨然一个小社会,既封闭又完善,这是三线厂的共同特征。
作为三线子弟,此刻再次站在这片熟悉又陌生的土地上,我深刻感受到一种特别的“宁静”,那不是万籁俱寂的安静,而是一种精神的宁静、一种穿透时空的力量。
这种宁静,是科学家们“不为物欲所惑、不为权势所屈、不为利益所移”的精神境界。在资料馆里,我看到放弃国外优渥待遇毅然归国的学者照片,他们眼神清澈,笑容坦然。邓稼先、钱学森……这些闪光的名字背后,是甘愿隐姓埋名、扎根深山的选择。他们并非没有物欲,而是被更高的追求所超越,有更坚定的信仰支撑;他们并非无视利益,而是在国家大义面前,个人得失轻如鸿毛。
在这种宁静的表象下,蕴藏着“披坚执锐显国威、金戈铁马铸国魂”的雷霆万钧。简陋的办公室里,算盘与计算器的碰撞迸发出震惊世界的巨响;昏暗的煤油灯下,密密麻麻的数据被编织成护卫国家的盾牌。没有超级计算机,他们用最原始的工具完成最复杂的运算;没有先进设备,他们用智慧和汗水浇灌出民族自强的花朵。这种在宁静中爆发的力量,比任何喧嚣都更加震撼人心——它让蘑菇云在戈壁滩上绽放,让《东方红》的旋律在太空回响,让中华民族挺直了脊梁。
站在邓稼先旧居前,简陋的居所与不朽的功勋形成鲜明对比,让人愈发懂得:最深沉的力量往往是静默的,最伟大的创造常常孕育于宁静。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宁静意味着在浮躁的社会氛围中保持清醒,守护好那份精神的定力,找到自己的人生坐标。
第二站来到北川,北川地震遗址的断壁残垣呈现出与参观两弹城时一种内在相通的震撼,如潮水般涌上心头。如果说两弹城诉说的是人在主动创造中展现的精神高度,那么北川遗址则见证了人在被动承受苦难时迸发的生命韧性。这两处场所,一为创造,一为承受,共同勾勒出中华民族精神谱系中最为深刻的两笔。
看着北川新县城的视频片,整洁的街道、崭新的建筑、人们脸上平和的笑容,与老县城里的废墟形成鲜明对比。这不仅仅是物理空间的重建,更是生命意志的胜利。它生动诠释了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辩证法——我们从不回避苦难的惨烈,所以我们保留遗址,铭记伤痛;我们也从不屈服于苦难的淫威,所以我们擦干眼泪,在废墟上重建家园。
第三站来到北川红军长征纪念馆,展馆里展陈的草鞋、破旧的军装、简陋的武器等,无声讲述着80多年前那场艰苦卓绝的战略转移。红军将士翻雪山、过草地,吃树皮、嚼草根,以超乎想象的毅力完成了二万五千里长征,为中国革命保存了宝贵的火种,一脉相承的坚韧精神变得更加清晰。
本次学习,从两弹城的“宁静创造”到北川的“坚韧承受”,再到红军长征的“绝境突围”,我看到了中华民族精神世界的完整图景——既有潜心钻研的沉静智慧,也有面对天崩地裂时的顽强不屈;既有创造奇迹的雄心,也有承受苦难的勇气。这份从绝境到新生的民族韧性,将如长征精神、“两弹一星”精神一样,融入我们的血脉,成为走向未来的不竭动力。
离去时,我回望这片曾经创造奇迹和饱受创伤的土地,心中涌起的已不仅仅是悲痛,更多的是敬意与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