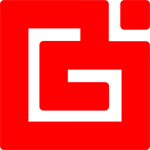https://kepu.gmw.cn/2026-01/26/content_38558032.htm
在地球上,有一种肉眼无法察觉的微球,直径仅20至30微米,比头发丝还要纤细。然而,在这毫厘之间的球体内部却蕴藏着精准狙杀肝癌细胞的巨大能量。它,就是钇-90玻璃微球,一款被誉为肝癌治疗“核武器”的尖端药物
曾几何时,这款救命药长期被国外企业垄断,“买不起、买不到、用不上”,成为中国肝癌患者面临的残酷现实。打破垄断,实现钇-90玻璃微球的国产化,不仅关乎技术创新,更直接连接着千家万户的生命健康。
自然界中,钇元素通常以稳定的钇-89形式存在,当钇-89的原子核捕获一个中子后,其内部结构发生改变,质子数不变,中子数增加一个,从而嬗变为具有放射性的钇-90。正是这多出的一个中子,让钇-90变得不稳定。
为了回归稳定,它会衰变释放出β射线。这种射线能量集中,但射程极短,仅约2.5毫米。“短程高能”的特性使其能精准摧毁肿瘤细胞的DNA,却几乎不损伤周围正常组织,宛若一位深入敌营的“精准杀手”。
秦山核电堆型丰富,特别是重水堆中子通量高,天生适合生产医用同位素,如何利用这座潜力巨大的“中子源工厂”,将稳定的钇-89转变为有医疗价值的放射性同位素——钇-90,成为秦山核电团队的新使命。
长期以来,医用同位素多依赖专用研究堆生产,让庞大的商用核电站跨界生产救命核药,一直是核能界的前沿课题。而且钇-90的半衰期仅有约64小时,这意味着它无法像半衰期长达数年的钴-60那样,利用机组大修窗口从容辐照,它需要一套极其精密、可靠的“不停堆换料”系统,在反应堆正常运行的同时,完成靶件的送入和取出。这相当于在核电站跳动的“心脏”中,搭建一条随用随通的“生命通道”,技术难度和风险极高。
挑战首先从寻找合适的“通道”开始。在堆芯内数百根林立排管构成的精密钢铁丛林中,团队最终锁定了一个直径仅3.4毫米、深达十几米的垂直孔道,但这仅仅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
如何在垂直孔道内将一根15米长、极易弯曲的生产通道毫发无伤地垂直旋入底部。一个二十多年前预埋的螺孔旋入深度需达50毫米,全程偏差不能超过10毫米……每一步都没有先例可循。团队开始了长达20个月的攻坚,他们自主研发勘测与安装装备在1:1模拟平台上进行了上千次演练,安装过程每一步都惊心动魄。
2024年,一个载入中国核医学史册的时刻到来——首批国产钇-90玻璃微球在秦山核电成功出堆,中国终于打破了长达三十年的垄断,团队自主研发的全套技术创造了四项国家发明专利。钇-90的成功像一把钥匙,打开了核能多元利用的新大门,它验证了商用堆生产高端核药的完整技术路线,预计在“十五五”期间,国产钇-90药品有望推向市场,将大大降低治疗成本,惠及广大肝癌患者。
从裂变到融合,从能源到健康,中国核工业人正用智慧与责任书写着从“核”而来、向“和”而生的新篇章。(2026-1-26)
相关报道:
中国科学技术馆微信公号:【智造未来】核反应堆“炼”出抗癌药!国产钇-90,让肝癌治疗不再“天价”
https://mp.weixin.qq.com/s/E1c6HPAFKZO8lgBav9cUqg